【本土语汇】“胡姬”与“兰花”
中国汉语“兰花”的应用自有其文学和美学历史的沉淀,新加坡华语“胡姬花”的使用也有其地域环境的合理性,本来可并行不悖,不料在1999年新加坡华语圈子掀起一场孰该用孰该废的争论。
跟以往一样,这场辩论自然也没有得出结论,两造各持己见,互不相让。支持使用“兰花”的作者,认为“胡姬”是英译名称,中国版的词典均未收入,也不在中国流行。作为小国寡民的新加坡采用“胡姬”,只能孤芳自赏,造成不便。支持保留“胡姬”使用的作者,以学者林万菁(1951-2024)的意见最具代表性,他认为“胡姬的使用具有时代的印记,也带有文化的负荷,保留胡姬一词意义深重”。
检验一个词语使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,还得从它产生的原因,传播的过程和最后被广泛接受的角度去探讨。
兰花、香兰、奥吉兰
1932年,马来亚胡姬学会主办的第二届胡姬花展览会,第一次有华人胡姬花种植者参与。当时新加坡五大华文报章,只有《星洲日报》关注和报道,它以“兰花”来指称胡姬;《新国民日报》则把它置于“星洲日记”栏目下,仅用一行文字,用的词语是“香兰”。
早期服务于新加坡华文报界在者,多数是中国南来的文人,他们沿袭中国用语习惯,以“兰花”指称胡姬花,不会令人感到意外。1935年出版的《新加坡指南》(潘醒侬编),在一篇介绍新加坡物产的文章中,却以音译词“奥吉兰”指称胡姬。
何以会产生这种现象?这是因为新加坡胡姬花的养殖是从白人开始,之后传入海峡华人圈,“奥吉”是英语orchid的闽南语音译。在闽南语主导的早期新加坡华社,选用“奥吉”作为日常口语词,是早期新加坡民间用语的现实。
这次胡姬花展之后,胡姬花报道的见报率越来越高,纵观这段时期的华文报章,胡姬花的指称五花八门,有沿袭中国传统采用“兰花”来表达;也有采用源自英语orchid的音译,比如“乌吉”“奥杰”“乌乞”“奥植”等;有者采用“兰”“花”或者“兰花”作为中心词,再配以其他词语作为修饰词,比如“乌桔花”“乌吉花”“乌结兰花”“野兰”“香兰花”“西洋兰花”“洋兰花”“寄生野兰”等,不一而足。报章在以“兰花”作为指称时,有时也会在“兰花”一词前面加上比如“寄生”“马来亚特产”等定语。
这种呈现多样性指称的情况,因为“胡姬”一词的出现而告终。
“胡姬”的诞生
“胡姬”的提出,颇具偶然性。根据林万菁引其老师施香沱(1906-1990)的说法,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林学大(1893-1963),在其胡姬花画作上以“胡姬”来称兰花。施香沱在文中并没有说明林学大何时在画上题词。不过,南艺目前藏有一一幅林学大作于1947年的画作《胡姬》,题词中出现“胡姬”一词。搜索当年的华文报章,首例以“胡姬”作为本地兰花的指称,出现在1948年3月25日的《南洋商报》一篇画评《几句忠言》中。


在历史考证上讲究的是“孤证不立”,林学大首创用“胡姬”一事以及时间点,我们也可从吴得先1949年的《守琴轩诗稿》(由南艺于2003年出版)得到佐证。从收在书中的《题在炎阿茝》这首诗的手稿中,可以清楚地看到吴得先(1893-1962)在林学大“胡姬”一词创用两年后,把原来写就的“胡茝”涂掉,进一步改为他认为音、义皆符合“Orchid”的音译词“阿茝”。施香沱文中说吴得先建议用“胡茝”而不同意林学大用“胡姬”一事,由此得到证实,同时也证明林学大创用“胡姬”这个说法其来有自。
时间证明林学大的选择是对的。“胡姬”后来被广泛采用,成为本地兰花指称的不二之选。1953年新加坡联营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《国语》四上(1953年版),其中一篇《名花展览》的课文,就采用“胡姬”一词,是新加坡课本使用的首例。“胡姬”获选为教学用语,让它在成为新加坡华语规范用语的路上,向前迈进一大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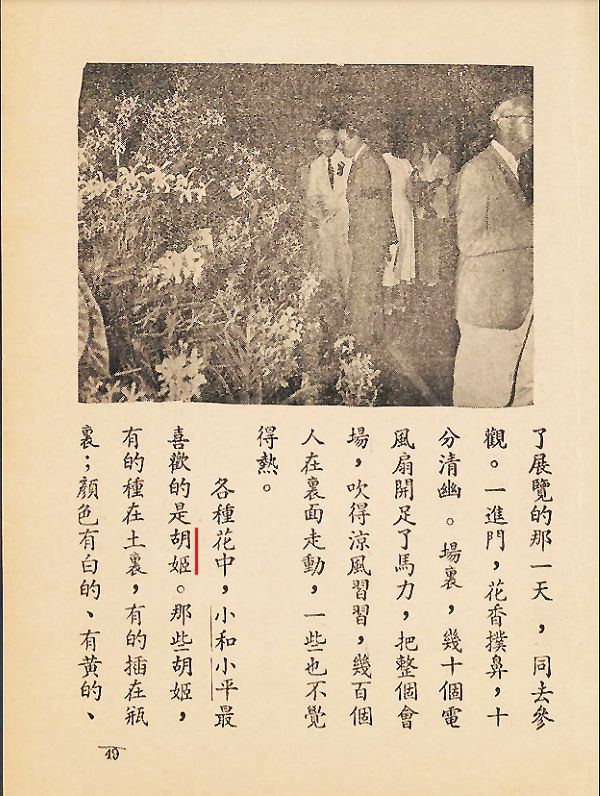
“胡姬”一词在新加坡的传播和使用,始终得到华文报章特别是教科书的助力,让它在不知不觉中,逐渐成为广泛接受的规范词。
胡姬花在新加坡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历史上,被赋予多重的象征意义和使命,具有非比寻常的价值,“胡姬”不仅是新加坡特色华语词汇,也普遍为东南亚华人接受,成为区域性的华语词汇。“胡姬”和“兰花”在新加坡语境中,各有不同的意涵,可以并行不悖。
许云樵,《文心雕虫》。新加坡:东南亚研究所,1973。 | |
邱克威,《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》。吉隆坡:华社文化中心,2018。 | |
汪惠迪,《狮城语文闲谈》。新加坡:联邦出版社,1995。 | |
林万菁,《论学杂著丛稿》。新加坡: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,2017。 | |
林万菁,《语言文字论集》。新加坡: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,1996。 | |
林恩和,《我城我语:新加坡地文志》。新加坡:长河书局,2018。 |










